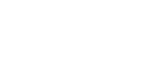第廿九章 约翰•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年七月十日生于法国诺阳(Noyon),这是一个主教城,离巴黎东北约七十哩。他父亲的性格相当刚直严厉,担任诺阳主教的助理,与当时的社会名流过往甚密。他母亲则以美貌与敬虔闻名,但是加尔文年轻时她便去世了。 加尔文在1528年至1533年间连续在奥尔良(Orleans)大学、部记(Bourges)大学、巴黎大学这三所著名学府念书,受的是当时法国最好的教育。他父亲打算栽培他从事法律,因为这行业通常能让人名利双收。但是年轻的加尔文不觉得有特别的呼召进入法律界,便转攻神学,发觉他的天赋和兴趣正适合他在神学的领域效力。一般人对加尔文的描写是害羞、不喜交际、工作极勤奋而规律、责任感极重;这使他作起事来格外带劲,又特别敬虔。
加尔文很早就显出一种特别的悟性,论证清晰而具说服力,又善于逻辑分析。由于他勤奋过人,所以心中蕴藏了丰富的知识,但是也使他的健康受损。他进步如此神速,以致有时受邀上台报告,他的同学也都把他当成是老师。那时加尔文仍是性格纯良的天主教徒,正预备作一个人文学家、律师或神职人员,前程似锦,却忽然转为抗议宗,把他的一生投给这艰难的教门,一生受逼迫。
他转向抗议宗之后,不到一年就成为巴黎的福音派领袖。这原本不是他的本意,甚至违背他的本意,但是他知识之渊博,谈吐之认真,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仍然暂时留在天主教,希望在体制内改革,不要在体制外革命。沙夫提醒我们,「每位改教领袖都是在天主教出生、受洗、坚信(confirm)、受教,又被天主教赶出来的;就好象每位使徒都是在会堂里受割礼、受训练,又被赶出会堂一样。」(注一)
加尔文刚成为改教领袖,热情与诚挚就遇到了考验,以致必须逃离巴黎、亡命他乡。教会历史学家沙夫对这段过程记载如下:「加尔文有位朋友尼可拉•科普(Nicholas Cop),是世居瑞士巴塞尔(Basel)的著名御医威廉•科普(William Cop)之子。尼可拉•科普于1533年十月十日被选为巴黎大学校长,照例要在那年的万圣节十一月一日于马斯林(Mathurins)教会当众发表就职演说。他请加尔文为这次演说撰稿,结果加尔文根据新约圣经为宗教改革请命,并且大胆攻击当时天主教经院派神学家,把他们说成是一群不明白福音的辩士......。巴黎大学的所尔波恩(Sorbonne)神学院与议会都认为这是对罗马教会宣战的檄文,所以定罪这篇讲稿,下令焚毁,并且明令如果有人捉到尼可拉•科普,不论生死皆赏三百银币。科普闻讯便马上投奔巴塞尔的亲戚。至于真正引发这波逼迫的加尔文,据说是以床单当绳子,从楼上的窗户缒到地上,装成园丁逃出巴黎,肩上还背着锄头,房间则被搜得不留一书一纸。从1534年十一月十日到1535年五月五日,有廿四位无辜的抗议宗信徒活活被焚于街市......,许多人被罚、下监、拷打,也有许多人逃往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其中便有加尔文与帝勒特(Du Tillet)。加尔文亡命于法国南部、瑞士、意大利达三年之久,以化名游行传道,直到了日内瓦才定居下来。」(注二)
1536年五月,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初版问世了;之后没多久,加尔文与帝勒特便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也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在《基督教要义》出版之前就到意大利了)。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一段时间,后来异教裁判所开始镇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两只他们眼中的毒蛇,他们就离开意大利,迂回而行,可能是取道亚索他(Asota),翻越圣大伯纳多(Great St. Bernard)山口,来到了瑞士。他曾经从巴塞尔回故乡诺阳城,把家里的事作个了结,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那时他同弟弟安东尼(Antonie)、妹妹玛莉(Marie)永别了法国,希望能在巴塞尔或斯特拉斯堡定居,作一个安静的学者,一生写作。从法国到瑞士,原本走洛林(Lorrain)这条路最直接,但是当时因为查理五世正和法兰西一世打仗,洛林这条路走不通,只得迂回而行,途中经过日内瓦。
加尔文本来只打算在日内瓦住一个晚上,但是神另有安排。日内瓦改教领袖法惹勒(Farel)体认到当时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到了存亡的关键,他知道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便直觉认定加尔文必能完成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拯救日内瓦脱离天主教的势力。沙夫曾经详述加尔文与法惹勒见面的情形如下:「法惹勒立刻拜访加尔文,好象从神领了圣旨一样,坚持要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加尔文以年幼、无经验、还要进修、生性害羞、内向、不适公众活动为由婉拒,但是这些理由都没用。法惹勒『心中异常火热,一心传扬福音』,威胁加尔文如果选择自己的兴趣,弃上主事工不顾,就必受全能神咒诅。这位福音勇士大无畏的精神撼动了加尔文,使他战兢不已,觉得『犹如神在高天之上向他伸手』。加尔文最后降服,受任作日内瓦福音派教会的牧师与教师。」(注三)
加尔文比路德与慈运理小二十五岁,所以能在他们立好的根基上建造,这是他得天独厚的地方。加尔文公开服事的头十年正是路德生涯中的最后十年,但是二人从未见过面。不过加尔文与墨兰顿私交甚笃,直到死前彼此仍有书信往来。
当加尔文在改教运动初露头角的时候,世人还无法确定路德倒底会成为一个大大成功的英雄,还是会成为一个大大失败的叛徒。路德已经把新观念提出来了,而加尔文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新观念整理成一个体系,好让这宝贵的成果得以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抗议宗运动缺乏一致性,本来差点要沦为教义的争论,并且会愈陷愈深,所幸日内瓦的改教领袖加尔文给它注入一股新动力,才使它免于下陷的命运。当时罗马天主教会上下一心,强势运作,不择手段,力求扑灭这从个北方兴起的各个抗议宗团体,慈运理见此危机,尝试联合所有抗议宗信徒抵挡公敌。他在马尔堡(Marburg)先是流泪恳请,接着不顾他与路德对「圣餐中基督怎样与会众同在」的歧见,向路德伸手表示彼此相合为一,但是路德受制于狭隘的教义,表示他的良心不容许他这样作,拒绝了慈运理的请求。
加尔文在瑞士工作,也有很多机会看到罗马天主教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认为抗议宗教会必须团结,并且为这样的事奔走。他曾经写信给英国的克蓝麦(Cranmer)说:「我渴望基督的肢体有一个神圣的相通(communion);至于我,如果有我能效劳之处,我很乐意为此效力,即使远渡重洋也在所不惜。」加尔文的著作、书信、门生发挥的影响力之大,世界各国均有强烈的感受;如果说加尔文对抗议宗运动有救亡图存之功,也不算夸大。
之后三十年间,加尔文一心一意推动宗教改革,全神贯注,别无旁骛。李德(Reed)说:「加尔文为宗教改革鞠躬尽瘁,奋战不懈,坚忍不拔,随时准备以身相殉。他真的将生命中每一滴脂油投入其中,毫不犹豫,毫不吝惜。加尔文献身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其专注、其坚毅、其舍己,翻遍历史也找不到第二人。」(注四)
加尔文是一位忠心、刚毅、不朽的人物,从使徒时代以来,基督的仆人恐怕没有人像他既深得人爱戴、敬佩、称赞、祝福,又深受人憎恨、厌恶、羞辱、咒诅。他生在论战激烈的时代,又站在西欧改教运动的高台,众目所视,各方攻击如林雨而来。宗教与宗派感情原本就是人类感情中最深刻、最强烈的,而人还活在世上,天性里有善也有恶,所以世人这样对待加尔文的教导与著作,也实在不足为奇。
加尔文年仅廿六岁便以拉丁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初版的内容是他思想体系重点的纲要。加尔文年纪轻轻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显示他的心智早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本书后来经过增订,篇幅达初版时的五倍,并且以法文出版;内容虽然有修订,但是没有一处偏离初版时提出的教义。这本书一出版,就独占螯头,公认是一本最能表达抗议宗主张、捍卫抗议宗理念的著作。其它书只是片面论述改教运动,这本书则是通盘讨论、一以贯之。李德说:
这本书是神所给宗教改革的一份礼物,价值难以言喻,抗议宗与天主教一同见证其价值,前者以最大的热诚迎之,后者以最毒的咒骂诅之。在巴黎和一些其它地方,巴黎大学的所尔波恩神学院下令焚烧这本书;在别的地方,它也引来最猛烈的口诛笔伐。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雷孟德(Florimond de Raemond)称之为「可兰经,异端的法典,使我们堕落的主因」,另外一位罗马天主教徒肯巴修特(Kampachulte)说:「这本书是教会的敌人共享的军械库,他们都从其中取得最精锐的武器」,又说:「宗教改革时期没有一本书像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一样,罗马天主教对它既惊恐害怕、全力抵挡,又严严搜寻。」从《基督教要义》一版紧接一版印行,就可以看出它多么受欢迎了。欧洲各个主要国家都有它的译本,改革宗教会都用它作训练与教导的材料,制定信条时也参考引用它。(注五)
华腓德说:「加尔文对人类的贡献很多,而且每一项贡献都很有份量,其中最大的贡献无疑就是他善用神的恩赐,使我们的信仰体系焕然一新,他的天份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新的生机。」(注六)
这本《基督教要义》一出版,就立刻受到抗议宗信徒的激赏与赞誉,认为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护卫基督教教义最清晰有力、最合逻辑、最具说服力的一本书。沙夫对这个现象有段描述说得好:「加尔文写这本《基督教要义》,原则上是为了有系统地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意义,但是也特别着眼于为福音派信仰辩解;这既是一本护教的书,也是一本实用的书,为了要保护抗议宗信徒,尤其是保护法国的抗议宗信徒,帮助他们抵挡当时来自各方的逼迫与毁谤」(注七)。整本书散发出强烈而真挚的感情、勇敢而严谨的论证,使人不得不承认,圣经确实是规范理性与传统的最高权威。这本书公认为十六世纪最伟大的一本书,加尔文主义也因此得以大规模传播。黎秋(Albrecht Ritschl)称之为「抗议宗的神学杰作」。华腓德博士说:「三世纪半之后,本书仍然毫无疑问是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教义著作」;他还说:「这本书光从文学角度来看,就足以在同类书中称为顶尖巨著;一个人如果有心要认识世界文学杰作,就必须熟悉这本书的内容。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在神学著作的地位,就好象希腊文学的修西狄第(Thucydides)、十八世纪英国历史界的吉朋(Gibbon)、哲学家中的柏拉图、史诗中的伊利亚德(Iliad)、戏剧家中的莎士比亚一样」(注八)。这本书使罗马天主教惊惶狼狈,使抗议宗大大团结,显明加尔文是抗议宗主义最有力的辩护者、罗马天主教最可畏的对手。这本书在英国受欢迎的程度几乎是空前的,各大学甚至用它作教科书,出版之后马上就被翻译成九种不同的欧洲语言。这本书近年来未受重视,主要是因为大部份的史书对它的介绍太少了。
《基督教要义》出版几个礼拜之后,德国改教领袖中的第三号人物布瑟写信给加尔文说:「显然主已经拣选你为他的器皿,要将最完满丰富的祝福赐给他的教会。」路德没有系统神学的著作;他的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是议题分散,而且许多只是针对当代的问题。福音派信仰需要有人作有系统的介绍,而这工作留给了加尔文。
加尔文虽然才华横溢,但是首要的工作还是神学。人很自然就把加尔文与奥古斯丁并列,认为他们是使徒保罗以来两位最伟大的基督教信仰体系阐释者。墨兰顿本身即是信义宗的「神学王子」,他称路德为「德国导师」,称加尔文为「那位正宗的神学家」。
如果有人觉得《基督教要义》用字过于严厉,那么他应该知道,用字严厉是那个时代神学争论的特征与弱点。加尔文处在一个好辩的时代,抗议宗信徒正与罗马天主教展开一场殊死战,有太多的事会激动人,使人失去耐心,而且都不是小事。不过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路德为了与主张意志自由的伊拉斯墨(Erasmus)辩论而写的《意志的枷锁》,就会发现加尔文的用字和路德相比,还算是温和的哩!何况讲到文字严厉,当时恐怕没有任何抗议宗信徒的著作能和罗马天主教针对抗议宗信徒所颁布的赶逐谕令和咒诅谕令相比。
除了《基督教要义》以外,加尔文也写了几乎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注释书,这套《加尔文圣经注释》翻译成英文共有五十五大册,再加上他的其它著作,总数之多令人乍舌,品质精良,无与伦比。《加尔文圣经注释》不但刚出版就被人认为是极优秀的一套圣经注释书,就是几百年后的今天,还是常常被最权威的圣经学者引用,这是其它老一辈的圣经注释书比不上的。加尔文毫无疑问是宗教改革时期最伟大的圣经注释家。路德是当时圣经翻译的第一把交椅,加尔文则是当时圣经注释的第一把交椅。
如果我们要评估《加尔文圣经注释》的真正价值,还有一件事不可忽略,就是加尔文用的解经原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李德说:「加尔文开风气之先,不用沿袭已久的寓意解经。说到寓意解经,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就盛行一时,教会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从俄利根(Origen)到路德也都认同,但是寓意解经至终使圣经沦为任人摆布的工具;人如果没有活泼的想象力,也无法踏入寓意解经的大门」(注九)。加尔文的解经严守分际,不逾越圣经作者的精意与字句,又假设圣经作者只有一个明确的思想,而且是用自然的日常用语来表达。他毫不留情地揭穿罗马天主教错谬的教义、腐败的规矩。他的著作鼓舞人心,使改教志士在这场争战中有了克敌致胜的武器。加尔文确保宗教改革的成果,使改教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甚至使它更上层楼,影响之大,笔墨难以形容。
加尔文是研究教父和经院(scholastic)哲学的专家。他受过当时最好的教育,精通拉丁文和法文,对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也相当了解。《加尔文圣经注释》最早出版时就有拉丁文和法文两种版本,解释详尽,立论公正,下笔坦诚,研判经文意义也力求平衡,避免极端,这都是这套注释书的独特之处。此外,法文在当时还是一种不成熟的语言,而加尔文的著作使法文有了固定的形式,而路德在翻译德文圣经的过程中也塑造了近代德文的风貌,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一个人的见证我们也不应该忽略,那就是与加尔文主义唱反调的阿民念。他的见证显然有其特别的价值,他说:「我鼓励我的学生除了研究圣经外,还要查考《加尔文圣经注释》。赫尔墨克(Helmick,荷兰神学家)推崇《加尔文圣经注释》,我比他更加推崇,因为我敢断言,没有另外一本圣经注释书能比得上它。从古教父到现在,教会的前辈先贤留下许多好书给我们,但是这套注释书值得我们更加重视。我承认他有独特的先知恩赐,很少人比得上他,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比得上他。」(注十)
加尔文还与抗议宗教会的领袖、王公、贵族有许多书信往来,这就使他的思想更加广传。这些书信还有三百多封保存至今,内容都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他对复杂的教会问题与神学问题发表看法,反复铺陈,气度恢弘。这样一来,加尔文就也引导了全欧洲宗教改革的方向,影响非常深远。
加尔文定居日内瓦二年之后,想和法惹勒推行一套相当严格的纪律,但是因为这套纪律太过严格,受到很大的反对,以致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日内瓦。加尔文来到德国西南部的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受到布瑟和德国改教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在那里安静地过了三年,从事教学、牧会、写作的工作,劳心劳力,都有明显的成效,也与信义宗主义有直接的接触。加尔文极欣赏信义宗的领袖,也觉得和信义宗的理念很近,不过对信义宗缺乏纪律、神职人员依附世上君王的印象不太好。从他的书信与各种著作可以看出,他后来非常热切地跟随德国改教的步调。当加尔文不在日内瓦的这段期间,事态日趋严重,甚至宗教改革的成果看起来好象岌岌可危,于是有人极力敦请加尔文回日内瓦。经过多次多方的恳请,加尔文终于答应,重拾他离开日内瓦之前的工作。从此以后,日内瓦湖畔的日内瓦城就成了加尔文的家,改革宗教会也从日内瓦传到全欧洲和美国。瑞士对全世界教会与国家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它面积所占的比例。
加尔文对日内瓦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如果不存偏见,光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加尔文主义转化人心的力量。杰出的教会历史家沙夫说:「日内瓦人无忧无虑,成天快活,喜欢在街市玩耍、跳舞、歌唱、化妆、荒宴,城内充满各种粗鲁、赌博、醉酒、淫乱、亵渎等类的恶事。娼妓是市政府许可的行业,老鸨备受推崇。老百姓普遍无知,神父不尽心教导,反而立下坏榜样。」我们只要研究当时的历史就知道,在加尔文去日内瓦的前夕,日内瓦的神职人员从修士到主教都还在犯罪,而且这些罪在今天都是可以判死刑的大罪。加尔文在日内瓦工作的结果,使日内瓦一扫往日的臭名,反倒以市容恬静、居民有序著称。当时来加尔文门下受教的人数以千计,其中有约翰•诺克斯,他说他在日内瓦看到「使徒时代以来,在地上所设立最完全属基督的学校。」
日内瓦经过加尔文的辛勤耕耘,已经成为人们受逼迫时的避难所,又成为改革宗信仰的训练营;全欧洲各国都有人流亡到日内瓦,等他们回国时都已经接受清楚的教导,完全明了宗教改革的原则,于是日内瓦成为改教的中心,在灵命上散发能力,在悟性上施行教导,引导邻近各国宗教改革的方向,塑造他们宗教改革的风貌。斑克鲁说:「加尔文对人类的贡献比梭伦(Solon)更真实。他比莱克尔古(Lycurgus)更舍己,他的精神也为日内瓦的各种制度注入一股持久的影响力,使它成为人民自由的坚固堡垒、民主制度的丰沃苗床,以迎接现代世界的来到。」(注十一)
加尔文对日内瓦的影响之大,还有一封天主教徒狄撒尔斯(de Sales)写给萨伏衣(Savoy)公爵的信函为证。他在这封信里说日内瓦是罗马天主教眼中异端的首都,应该要镇压。他说:
所有的异端都以日内瓦为他们宗教的避难所......。全欧洲再没有别的城市比它更方便鼓励异端滋生了;它是法国、意大利、德国的门户,那里各国的人都有,例如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甚至更远的国家。此外,大家都知道它是培养牧师的地方,光是去年一年,就训练出二十名牧师给法国,甚至还提供牧师给英国;此外,它庞大的印刷设备使邪书泛滥全世界,甚至用公费印刷,这一切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一切大举对抗教宗和枢机主教的阴谋都是在日内瓦发起的,全欧洲也没有别的城市像它这么广纳各阶层的背道者,其中包括修会内的圣职人员,也包括修会外的圣职人员。所以我的结论是:毁掉日内瓦,异端就会消失。(注十二)
还有一个见证来自抗议宗的死敌,就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他曾经写信给法王说:「这城(日内瓦)是法兰西一切灾难的根源、罗马最可怕的仇敌;我随时都准备好了,要加入消灭日内瓦的行列,全力以赴。」当亚尔伐公爵率领军队经过日内瓦的时候,教宗庇乌(Pius)五世甚至请他改变原定路线,转攻日内瓦,要他「捣毁那恶魔与背道者的巢穴」。
著名的日内瓦学院(academy of Geneva)创立于1558年,连加尔文在内共有十位教授,每位都才思敏捷、勇于任事,课程包括文法、逻辑、数学、物理、音乐、古语文。学院办学成效卓著,头一年就有九百多名学生注册,大部份都是从欧洲各国来日内瓦避难的,而另外差不多还有九百多名学生专门来上加尔文的神学课程。他们都准备一旦学成回国,就按照日内瓦的模式传福音、教导信徒、建立教会。二百年来,日内瓦学院一直是改革宗神学的主要学府和出版重镇。
加尔文是第一个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的改教领袖,这是加尔文提出的另一个极宝贵的原则。宗教改革在德国是由君王决定的,在瑞士是由人民决定的,不过无论是德国或是瑞士,统治者与大部份人民的看法都相去不远,所以两地的宗教改革并没有重大差异,只是瑞士的改教领袖住在民主共和体制的日内瓦,便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发展出一个自由的教会,而路德与墨兰顿生来崇敬君主制度和德意志帝国,便教导信徒在政治上要顺服政府,教会也就因此受政治权柄的管辖了。
加尔文于1564年过世,享年五十五岁,可谓英年早逝,他的工作由他的密友伯撒(Beza)接续。伯撒描述加尔文之死为「寿终正寝」。他说:「正当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位最灿烂的星辰、教会的灯台,就被接回天家了。当夜加尔文与世长辞,隔日举市哀恸,因为政府失去了最智慧的公民,教会失去了最忠实的牧者,学院失去了最卓越的教师。」
哈克奈斯(Harkness)教授在一本他的近著中说:「加尔文一生清贫,室无华饰,衣装朴素,人有急难便慷慨解囊,却很少花钱为自己打点,有一次日内瓦议会送他一件大衣,一方面表示对他的敬意,一方面也让他可以御寒过冬。这份礼物加尔文欣然接受,但是另外有几次教会要提供他金钱援助,他则不受,也谢绝微薄薪金之外的任何馈赠。他在最后那场病中,教会想要替他付医药费,但是被他拒绝。他的理由是他既然已经不能工作,连领薪水都觉得很勉强了,更不能接受教会这样的好意。他过世之后,属灵的遗产价值连城,无法估算,属世的遗产却只在一千五百元到二千元之间。」(注十三)
沙夫说:「世上有一种人,只能让人尊敬景仰,却不能让人喜欢;加尔文就是这种人。他不容许人和他过分亲近、过份熟识,但是人和他深交之后,就会长进。人愈认识他,就愈敬仰尊崇他。」沙夫论到加尔文的死是这样说的:「加尔文明白表示他的葬礼严禁虚荣,坟墓也不立碑。他希望比照摩西下葬的方式,好使他日后绝对不可能成为偶像,这正与他『降卑人,高举神』的神学相合」(注十四)。今天甚至在日内瓦都没有人知道加尔文的墓地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有一个刻有J. C.(就是约翰•加尔文的缩写)的简单石碑,以满足游客的好奇。坟墓也不立碑是加尔文自己的请求,不过正如毛里斯(S. L. Morris)说的,加尔文真正的纪念碑是「世上每个民主共和国,世界各国的公共学校制度,和『全世界持守长老会思想体系的改革宗教会』。」
哈克奈斯有时下笔对加尔文并不友善,不过他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有许多人只看到加尔文面容严肃,却忽略了他向教会许多会友都表现温柔,而且几乎是女性的温柔。他与忧伤的人同悲,与喜乐的人同乐;他写信给那些因家人过世哀伤的人,有些信显示他非常柔细地体会对方的心情,堪称同类作品中的杰作。有时候别人家有喜事,或是有婴孩诞生,他也不会冷冰冰地不闻不问,而是相当热情地关切。他虽然常常有大事要办,却也不忘在街头停下来,拍拍小学生肩膀,说些鼓励的话。反对他的人称他为教皇、国王、加尔夫(caliph,译注:回教国王),但是他的朋友只把他当成弟兄、亲爱的领袖」(注十五)。在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马上就要来拜访你,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大笑一场。」
现在我们必须谈一件发生在加尔文身上的事;这件事对他的美名或多或少是个阴影,也使他被扣上不宽容、迫害人的罪名。这就是瑟维特(Servetus)事件。有一位瑟维特死于加尔文在日内瓦工作期间。这件事作错了,这是每个人都承认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毫无瑕疵,就是罪人的救主,其余的人都有软弱的记号,使人绝对不至于成为别人的偶像。
不过一般人在这件事上对加尔文的批评常常过份严厉,好象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加尔文一个人身上似的。事实上瑟维特是经过法院两个月以上的审理,并且由全体市议会判决,才被烧死的。这都是按照当时全体基督教界公认的法律执行的,而且加尔文根本没有极力主张动用严刑,反倒是极力建议行刑时用刀剑即可,不要动用火刑,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我们不应该只用我们二十世纪的高标准来严加批判加尔文和他当时的人,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以他们十六世纪的背景来看这件事。我们看到今天的政治宽容、宗教宽容、监狱改革、废止奴隶制度、禁止贩奴、废除封建制度、禁施火刑于女巫、改善穷人生活条件等进步现象,这都是基督教后来才提倡的;这些教导经过一段时日才出现,也更显出这些教导的真实。当时一般人提出不宽容的主张,甚至表现出不宽容的作法,我们今天来看是错谬,不过这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普遍的错谬。平心而论,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怀疑他们的性格与动机,更不应该因此对他们的教义存有成见,以致当他们讨论那些更重要的问题时,我们也都充耳不闻。
那时抗议宗信徒刚刚挣脱罗马天主教的辖制,常在险恶的环境中力求自保,难免被迫用不宽容抵抗不宽容。在十六、七世纪,全欧洲不分君王百姓,都一致公认护卫正统、惩罚异端不但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责任,甚至主张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将顽固的异端份子或亵渎份子处死,才能确保社会大众不受他们危害。抗议宗信徒与天主教主要的差别只是对异端有不同的定义,而且处罚异端份子比天主教温和许多。异端在当时是干犯全体社会的罪,有时候甚至比杀人罪更严重,因为杀人者只杀人的身体,而异端份子却灭人的灵魂。今天我们走到另一个极端,大多数信徒判断真理或谬误的尺度太宽松了,有时候甚至根本漠不关心。到了十八世纪,不宽容的精神才逐渐式微,英国与荷兰的抗议宗率先倡导人民应该有更多政治自由与信仰自由,美国的宪法更将这样的理论付诸实现,使基督教所有宗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证他们享有相同的权利。
当时每一位改教领袖都完全认同加尔文处理瑟维特事件的整个过程。信义宗的神学领袖墨兰顿完全支持加尔文与日内瓦议会的处置,甚至引为模范。瑟维特死后约一年,墨兰顿写信给加尔文说:「我已经读了你清楚驳斥瑟维特的书,瑟维特的亵渎真是可怕......。教会不但现在要感谢你,就是千秋万代之后还是要感谢你。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也肯定日内瓦市府当局经过正式审理程序惩罚这亵渎者的作法。这件事作得对。」德国的改教领袖布瑟、慈运理的密友与工作继承人布灵格、日内瓦的法惹勒、伯撒都支持加尔文。路德与慈运理那时已经过世了,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如果在世,是否会同意瑟维特被处火刑,不过路德与威丁堡(Wittenberg)的神学家们都曾经批准几位德国重洗派(Anabaptist)的死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危险的异端。他们还补充说明,表示这样刑罚他们固然残忍,但是如果纵容他们咒骂神话语的职事、毁灭地上的国家,那就更残忍了。瑞士曾经有六名重洗派被处死刑,当时慈运理也没有表示反对。几百年来大家对这事的看法有很大的转变:十六世纪最优秀的人物都完全认同瑟维特事件的处理方式;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却刚好相反。
前面提过,那时罗马天主教岂止不宽容抗议宗信徒,简直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逼迫抗议宗信徒上了,好象不逼迫抗议宗信徒就活不下去似的;抗议宗信徒为求自保,也被迫有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沙夫叙述罗马天主教实际逼迫抗议宗信徒的情形如下:
我们只要来看下面这些事就好:英诺森(Innocent)三世是有史以来品德最高尚、功绩最丰伟的教宗之一,扑灭亚勒比根斯(Albigenses)与瓦勒度派(Waldenses)的谕令却是他批准的;西班牙的异教裁判所甚至把拷打异教徒和异教徒示众游行当成是宗教庆典;荷兰在亚尔伐公爵治下(1567-1573)有五万多名抗议宗信徒被处决;在血腥玛莉皇后治下,司密斯婓尔(Smithfield)一地便有数百名殉道者被烧死;无辜的瓦勒度派在法国和皮德蒙两地一再遭受大举的迫害,以致他们向天呼喊,求神伸冤。有人企图为罗马天主教辩解,但是他们一味把责任推给政府是没用的。教宗贵格利(Gregory)十三世不但用赞美颂(Te Deum)纪念圣巴多罗买日的大屠杀,甚至还故意作纪念章,把『胡格诺派大屠杀事件』说成是神怒气的天使作的,想把这件事弄成一桩足以传扬万代的神迹。」(注十六)
沙夫博士又说:「罗马天主教今天已经没有权力用火与剑逼迫人了,即使有权力这样作,意愿也不高了。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有些高层人士已经清楚表明他们不认同逼迫的原则,这在充分享有宗教自由的美国尤其明显,但是罗马教廷却从来没有正式否认当初罗马天主教逼迫异端所根据的理论;相反的,宗教改革之后仍有几个教宗认可当初逼迫异端所根据的理论......。教宗庇乌九世于1864年的谬说要录(Syllabus)中清楚定罪许多当时的谬误,其中就包括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而1870年的梵蒂冈谕文不但宣告庇乌九世的正式言论为无谬,而且不顾教宗何挪留一世(Honorius I)的先例(译注),还是宣告庇乌九世所有前后任教宗的正式言论也都无谬」(注十七)。沙夫还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如果罗马天主教定罪加尔文,那是因为他们恨他;但是如果罗马天主教在瑟维特事件上定罪加尔文,那可就是定罪加尔文效法他们自己的榜样了。」
瑟维特是西班牙人,反对基督教,不管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抗议宗他都反对。沙夫称他为「狂热不止,冒称改教,实为泛神论,是十六世纪最无耻的异端,甚至亵渎神」(注十八)。沙夫在另外一个地方称瑟维特「自大,桀骜,好争,记仇,喜用不敬言辞,欺瞒,虚伪」,又说瑟维特性喜谩骂、蛮不讲理,罗马天主教与改教领袖都曾经被他糟蹋(注十九)。布灵格说即使撒但自己从地狱里出来,咒骂三位一体神用的亵渎话也比不上这个西班牙人。罗马天主教的白勒色(Bolsec)写过一本关于加尔文的书,里面提到瑟维特是一个「非常桀傲不逊的人」、「荒谬的异端份子」,应该灭绝。
瑟维特是从法国的维安(Vienne)逃到日内瓦的。当瑟维特在日内瓦受审的时候,维安的罗马天主教审判官传来一封信给日内瓦议会,并且附上维安宣判瑟维特死刑的正式文件,请日内瓦议会将瑟维特遣返维安行刑,又表示维安当局已经把这个死刑执行在瑟维特的刍像和著作上了。议会回绝这请求,但是答应秉公处理这个案件。瑟维特本人宁愿在日内瓦受审,因为维安已经把柴堆好了,他回维安必死无疑。维安当局传来这封信,或许会使日内瓦议会更热心维护正统信仰,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这件事上落在罗马天主教后面。
瑟维特去日内瓦之前,曾经多次写信给加尔文,希望博得加尔文的注意。加尔文有段时间曾经详细回信给瑟维特,但是发觉无效后就停笔了。可是瑟维特仍然继续写信给加尔文,而且语气愈来愈傲慢,甚至侮蔑。他认为加尔文是正统抗议宗的教皇,一心一意要让加尔文改变信仰,否则就要把他扳倒。当瑟维特到达日内瓦的时候,正逢反对加尔文的自由派控制市议会。瑟维特表面上加入此党,实际上想藉此把加尔文赶走。加尔文显然察觉到这个危险,并且绝对不容许他在日内瓦散布异端邪说,所以他以除灭这个危险人物为己任,好叫他不能危害大众;又下定决心,如果不能让他改变立场,就要让他受到应得的惩罚。瑟维特马上被捕受审,加尔文主审神学部份,结果瑟维特被判有罪,罪名分别是「在基要真理上是异端」、「虚伪」、「亵渎」。这个审判经过很长的时间,审判过程中瑟维特的胆子愈来愈大,甚至想用各种谩骂压过加尔文的气势(注二十)。这个案子最后送交民事庭,结果裁定瑟维特要处以火刑。加尔文曾经请求议会用刀不用火,但是议会没有采纳,所以瑟维特受火刑的责任最后不在加尔文,而在议会。
陶莫格(E. Doumergue)博士是研究加尔文的专家,他写《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一书,毫无疑问是有关加尔文最详尽、最权威的著作。他对瑟维特事件有段话说:「瑟维特到了日内瓦之后,加尔文把他逮捕,并且向法院具名控诉。加尔文确实希望瑟维特被判死刑,但不是火刑。1553年八月廿日加尔文写信给法惹勒说:『我希望瑟维特被定死罪,但是希望能免了他火刑的痛苦』。法惹勒九月八日回信表示『不很赞成加尔文这种心软的态度』,接着又警告加尔文小心,不要『因为希望减缓瑟维特受火刑的残酷,而使你把最大的仇敌当成朋友。我恳请你在这件事上自制,好让以后没有人胆敢发表这种教义,或是以身试法,想和这人一样闯这么大的祸,为害这么久,却还安好无事』。
加尔文并没有因为法惹勒这番话改变想法,但是也没有办法说服法惹勒;十月廿六日加尔文再写信给法惹勒说:『明天就是瑟维特行刑的日子了。我们已经尽全力要求改变行刑的方式了,但是没有成功;至于为什么没有成功,等我们见面再谈。』」(注廿一)
这样看来,加尔文最引人非议的瑟维特被焚事件,其实加尔文自己也相当反对。他不必为此负责,因为他已经尽全力救瑟维特免于火刑了。这火刑架上的柴堆和硝烟使人得着许多指责加尔文的把柄,有的振振有辞,有的根本条理不清,其实如果瑟维特不是受火刑,恐怕就是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无人过问。
陶莫格博士接着说瑟维特事件是「时代的错误,责任不应该特别落在加尔文身上。瑟维特被宣判死刑之前,瑞士众教会都事先被征询过意见,有些教会和加尔文完全没有交情,但是都投赞成票......。此外,审判结果是议会宣判的,而议会中多数是与加尔文素不和睦的自由派思想家。」(注廿二)
由加尔文日后的书信可以清楚看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为这件事负责。「自从瑟维特被定罪为异端之后,我从来没有对他应该受什么刑罚讲过一句话,这是每一个诚实的人能为我作见证的」(注廿三)。
加尔文在瑟维特被捕之前和受审之初,都曾经根据「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利廿四16)这条摩西律法,主张瑟维特要被治死。加尔文认为这条律法的效力和十诫相同,也适用于异端;但是他完全让议会决定这个案件应该如何判决。他认为瑟维特是宗教改革的大敌,并且真实相信「政府有权利与责任决定,干犯教会的罪行应该受怎样的惩罚」。加尔文也觉得神呼召他洁净教会,使教会不至被诸样人事物玷污而腐化。他直到过世的那一天,都没有改变这样的看法,也不后悔他对瑟维特所作的事。
荷兰的凯波尔博士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神学家,他几年前在美国演讲,其中有段话谈到这件事,值得在此一提:
政府有义务铲除一切伪宗教和偶像崇拜。这不是加尔文主义的创见,从康斯坦丁大帝开始就有这种观念了。在康斯坦丁大帝之前,罗马皇帝是异教徒,他们逼迫基督徒的作为令人发指;到了康斯坦丁大帝,则反过来铲除异教。从那时候开始,每位罗马天主教神学家都为这种制度辩护,每位信奉基督教的君王也都遵行。在路德与加尔文的时代,一般人都确信遵行这种制度就是奉行真理。当时每位著名神学家,尤其是墨兰顿,都赞同瑟维特被处火刑。从抗议宗的角度来看,信义宗在莱比锡(Leipzig)为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克里尔(Kreel)所设的绞刑台,更应该被谴责千万倍才对。
宗教改革时期,成千上万的加尔文主义者走向绞刑台、火刑堆,牺牲殉道(信义宗与天主教的殉道者人数却是寥寥无几),历史对这样的事实好象视而不见,却专挑瑟维特事件的毛病,称之为极恶之罪(crimen nefandum),一直用这件事指责加尔文和他的跟随者,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而这种不公平的态度造成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虽然如此,我不但为这火刑感到遗憾,也绝对不认同这种作法;不过我认为这不是加尔文主义的特征,而是加尔文主义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是加尔文主义也没能完全脱离这样的错误。(注廿四)
所以我们如果要公正看待瑟维特事件,就应该考虑十六世纪的背景,也应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第一,其他改教领袖都同意这件事;其次,社会大众普遍痛恨妥协,认为妥协就表示对真理漠不关心,也认为异端份子和亵渎者如果不肯悔改,就应该处死;此外,我们还可以想到罗马天主教也同样判瑟维特火刑、瑟维特的人品和他对加尔文的态度、瑟维特存心到日内瓦找麻烦,而且判决权在民事庭,不是加尔文所能掌控,加尔文也请求用较轻的行刑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有许多外在环境使我们可以再斟酌一下我们对加尔文的指责;二、不管怎么说,加尔文是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才作这件事。我们爱从哪个角度看加尔文都可以。克伦威尔在别人为他画肖像时说:「好看的、不好看的,全都画进来吧!」,我们如果要给加尔文画肖像,也应该这样;而正如沙夫说的:「加尔文和人熟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好多了」。加尔文毫无疑问是神所差遣、要来震撼世界的,这种人物在历史上出现的次数寥寥可数。
(注一) Schaff, The Swiss Reformation, p.312.
(注二) 同上,p.322.
(注三) 同上,p.348.
(注四) R. C. Reed, Calvin Memorial Addresses, p.34.
(注五) 同上,p. 20.
(注六) Warfield, Article, The Theology of Calvin, p.1.
(注七) Schaff, The Swiss Reformation, p.330.
(注八) Warfield, Calvin and Calvinism, pp. 8, 374.
(注九) Reed, Calvin Memorial Addresses, p.22.
(注十) Quoted by James Orr, Calvin Memorial Addresses, p. 92.
(注十一) Bancroft, Miscelanies, p. 406.
(注十二) Vie de ste, Francois de sales, par son, Neveu, p.20.
(注十三) Harkness, John Calvin, The Man and His Ethics, p.54
(注十四) Schaff, Swiss Reformation, p.826.
(注十五) Harkness, John Calvin, The Man and His Ethics, p.55.
(注十六) Schaff, The Swiss Reformation, II., p. 698.
(注十七) 同上,II., p.669.
(译注) 何挪留一世曾经支持「基督一志说」,但是后任教宗定罪这种说法,而且康士坦丁堡会议(Councils of Constantinpole)曾经因此判何挪留一世为异端,这使教皇无谬说(Infallibility of the Pope)难以自圆其说;参《当代神学辞典》(校园出版社,858页)。
(注十八) Schaff, The Creeds of Christiandom, I., p.464.
(注十九) Schaff, The Swiss Reformation, II., p.787.
(注二十) 同上,II., p.778.
(注廿一) Doumergue, Opera XIV, pp. 590, 613-657.
(注廿二) Doumergue, Article, What Ought to be Known About Calvin, in Evangelical Quaterly, Jan., 1929.
(注廿三) Doumergue, Opera, VIII., p.461.
(注廿四) A. Kuyper, Calvinism, 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