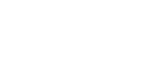第三十章 结论
我们已经对加尔文主义体系作了一番详细的考察,并且看见它对教会、国家、社会、教育的影响。我们仔细探讨了反对加尔文主义的常见理由,也仔细查考了加尔文主义的实用价值。现在我们只要对加尔文主义再作一点整体观察,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讨论了。
如果我们想检验一个人,或是检验一个思想体系,用主基督说的「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句话作标准,一定错不了。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者都欢迎这种检验方式。一个人如果遵行改革宗信仰,他们生命的影响力就是加尔文主义最有力的证据。司密斯说加尔文主义「洋溢着从神而来的活力,创建了近代世界,培育出无数的英雄、圣徒、殉道者。历史从果子判断树,认为加尔文主义称得上是基督教界最伟大信条」(注一)。历史学家公认加尔文主义能塑造人的品格、宣扬自由理念,对个人与国家都有益;就这方面来说,没有别的信仰体系能比得上它。
我们翻开美国历史上的名人录,就会发现有许多总统、国会议员、法官、作家、编辑、教师、商人信奉加尔文主义,比例上远远超过其它宗派。每位公正的历史家都会承认,因为抗议宗主义起来抵挡罗马天主教,才使现代世界得以初尝真正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果实,而那些最自由的国家,也几乎都是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国家。加尔文主义造成一股风潮,使人起来要追求信仰自由、政治自由、并且要从其中得生命。我们从近代历史可以看出,每个已经预备好的国家都接受了这股风潮。我们如果把英国、苏格兰、美国和从来没有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较,马上就可看出加尔文主义的实际果效。罗马天主教国家经济与道德衰败,各方面都走下坡。
我们只要对教会历史或抗议宗的重要教义有一点研究,就会立刻看出:加尔文主义在当时不但促成了宗教改革,也使它的成果得以保存。我们如果熟知欧美历史,就会完全同意甘宁汉博士所说「除了使徒保罗以外,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就是约翰•加尔文」这番惊人之语了。司密斯博士说得好:「我们只要想到加尔文主义者的血汗、祷告和教导,使我们有了社会自由、抗议宗信仰、基督教家庭这三样果实,就一定能塞住一切诽谤加尔文主义之人的口。读者如果细心,应该可以看出这三样祝福也是现代世界一切至美至善事物的根源,也会惊讶这句话其实在暗示今天基督教文明主要是加尔文主义的果实。」(注二)
如果我们说加尔文主义是圣徒与英雄的信条,这也只是重述历史清楚的见证罢了。佛劳德说:「加尔文主义者是唯一不畏争战的抗议宗信徒,他们因着信仰而有勇气为宗教改革站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现象,反正这是事实就对了。如果没有他们,改教运动早就失败了。」当成千上万的人还在受属灵的压制,而英国、苏格兰、荷兰、瑞士的抗议宗主义又必须以武力自卫的时候,唯有加尔文主义证明自己是唯一能与罗马天主教强大势力抗衡甚至将它摧毁的教义体系。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信徒殉道者数目之多,远超过其它宗派,这是加尔文主义引以为荣的表现之一。
1896年的循道会大会有一篇对长老会联会的演讲,其中有一段话很有风度:「贵教会带给世人一幅振奋人心的壮观景象,值得我们怀念。贵教会不是一批独行侠,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而是一群世代忠心、可以随时为主和主的真理欢然下监受死的圣徒。你们认为这是一项殊荣,是你们产业中最宝贵的一份,确实如此。」马飞治说:「加尔文主义者几乎都愿意为信仰光荣牺牲,甚至宁可赴汤蹈火也不愿背叛信仰、不肯在良心上稍留玷污的信徒,不分男女,都不是只跟从神的儿子而已。跟从神的儿子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也都还跟从一位神的仆人,就是使日内瓦成为欧洲之光的约翰•加尔文」(注三)。这体系靠神充满能力,也从神结实累累,世人应该满心感谢。这些年间世人确实逐渐体认其宝贵,只是难以回报。
我们已经说过,加尔文主义神学孕育出一批爱好自由的人民。加尔文主义兴盛之地,专制独裁便无法存留。可能读者已经想到,加尔文主义很早就带下革命性的教会治理方式了,这方式使它的会友不是受由某个人或某群人指派的人管理与服事,而是由他们自己所选出的牧师与同工来管理他们。这样一来,信仰就在信徒的身边,而不是高高在上了。关于这种治理方式的效率,有一个惊人的见证来自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纽约大主教休斯(Hughes);他说:「虽然我有权力可以说长老会总会的权柄是一种僭越的行为,但我还是得和每位熟悉它组织运作的人一同说:就治理大众事务与政治事务的功用而言,它的结构与国会相比毫不逊色。它以辐射中心的原理运作,在美国没有别的宗派能与它相比。」(注四)
从教会的自由与责任到国家的自由与责任,其间不过一步;历史告诉我们,加尔文主义者勇于捍卫自由理念,无人能比。
瓦波顿说:「加尔文主义不是象牙塔里的理论信条。反对它的人遽下断言,说它鼓励人主张宿命论、对周围之人的需要冷眼旁观,看到社会中罪恶嚣张,好象伤口腐烂,也漠不关心;但其实不是这样」(注五)。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都带来惊人的道德改变。加尔文主义者在清心、节制、勤奋、周济穷人的事上是无可伦比的。
佛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是英国很著名的历史家与学者,担任牛津大学历史教授多年。尽管他接受另一种神学体系,尽管他的著作常使人说他反对加尔文主义,但是他对加尔文主义并无偏见。这些年间经常有人对加尔文主义作无谓的攻击,这位公正的学者忍不住要有所回应。
佛劳德说:「我要请你仔细思量,如果加尔文主义真的像近代启蒙主义所说,是僵硬的信条、不讲道理,那么它从前怎么能吸引一批最伟大的人物跟随它呢?如果它真的像有人所说,因为反对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对道德有杀伤力,那么为什么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第一个特征就是使人意识到犯罪不只得罪人,也同样得罪神,又使道德律成为个人与国家的生活规范呢?我还要问你:如果它是奴役人理智的信条,那么为什么还能持续激发出最英勇的行为,进而摧毁不公义的权势呢?当一切其它的东西都灭没、爱国心没落、人的勇气溃灭、人的理智如吉朋所说『带着笑容与叹息』关在密室自得其乐地玩哲学,或是走出来与人一同迷信敬拜、各种柔细的感情和自以为是的敬虔受迷信的辖制,浑然不知谎言与真理还有区别时,只有那被称为会奴役人的加尔文主义以各种方式站在第一线对抗迷妄与虚伪,宁可像火石被磨成粉但发出光热,也不愿在暴力前屈膝,受诱惑而丧志软化。」(注六)
佛劳德也举沉默者威廉、路德、加尔文、诺克斯、科利尼、克伦威尔、密尔敦(Milton)和本仁(Bunyan)为例,说他们「具有一切使人性高尚伟大的特质。他们正直的生命和慑人的悟性相称,致力于公众事务时不掺一点私心,职责所驱时便铁面无私,但是心中柔细如妇女,坦白,真实,爽朗,幽默,丝毫不乖戾狂热,并且能发号施令,使欧洲每一个勇敢忠信之士发出共鸣。」(注七)
我们也留意到加尔文主义是一个传福音的力量。任何信仰的教义体系都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测试方法,就是「与其它教义体系相比,能否证明自己传福音给世人时有果效?」。拯救罪人、使罪人悔改,是教会在今世的主要目的。一个教义体系如果够不上这项考验,那么它无论在其它方面多么迎合人心,也不能被教会接纳。
大家公认宗教改革是新约时代以来最伟大、最真实的宗教复兴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从路德、加尔文、慈运理传讲纯正预定论开始的。1555年抗议宗远赴巴西的首次海外宣教大业也要归功于加尔文和科利尼将军。不过这次行动最后确实没有成功,而欧洲的宗教战争使宣教事工耽搁了相当长的时间。
著名的英国浸信会牧师司布真(C. H. Spurgeon, 1834-1892)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他曾经说过:「我从不以自称信奉加尔文主义为耻,我也毫不犹豫使用浸礼派(Baptist)的称号;但是如果有人问我的信条,我的回答是『耶稣基督』。」他又说:「我们许多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讲道者并没有真正喂养神的百姓。他们相信神拣选,但是不传讲这道理。他们认为神的救赎有特定对象,但是把这道理锁在他们放教义的柜子里,从不把它拿出来用在服事上。他们持守圣徒永蒙保守的道理,但是他们一直『保守』自己在这事上闭口不言。他们相信有效恩召这回事,但是认为自己没有蒙『恩召』要常常去传讲这道理。我们发觉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把他们所相信的直接传讲出来。你可能听了他们五十次讲道,还不知道福音的教义,也不知道他们对救恩的整体看法。这样一来,神的百姓就得不到供应,以致灵里贫瘠。」(注八)
当我们来研究海外宣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加尔文主义曾经是神在使福音传到异教国家时所使用的最重要工具。一个人即使反对加尔文主义,但是只要他还算开明,都会承认加尔文派的神学思想和保罗的主张是多么的一致,而这位保罗就是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如果我们打开抗议宗海外宣教英雄簿,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曾经作过加尔文的门徒,几乎没有例外。去印度的马廷(Martyn),去非洲的李文斯顿(Livingstone)与摩法特(Moffat),去中国的马礼逊(Morrison),去南洋的培顿(Paton),以及许其他的宣教勇士,他们都承认并且持守加尔文主义,而且他们不是安安静静地信奉加尔文主义,而是充满活力。加尔文主义对于他们不单是信条,也是行动。
论到海外宣教,李彻尔博士曾说:「虽然我们和所有其他在主里的肢体一样,想到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源远比过去更多,异教世界的需要又如此之大,而我们没能在这方面作得更多,都觉得应该感到悲哀,但是加尔文主义者至少有件事可以感谢神,就是神让我们可敬的先祖在建立全球宣教大业上踏出如此美好的第一步。今天加尔文教会在海外宣教上领受的恩赐很多......加尔文教会有幸与每个重要的非基督教信仰有对话,把福音带到他们面前让他们选择,也使福音更多飘洋过海,传到更多地方、更多国家、更多人民、更多语言群体中间。」(注九)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几个世纪以来,加尔文主义无所畏惧,坚守纯正教义,与人辩论铿锵有声,已经成为基督教会的真实力量。加尔文主义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用比较高的标准训练教牧人员,这在引人归主、收割主庄稼上产生很大的果效,而且不是使人一时激动兴奋,而是使人立下永恒誓约。如果从所结的果子来判断树,加尔文主义已证明自己是一股极其伟大的传福音的力量。
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人是无法诚实面对历史见证的。现代文明史中,实在应该有一份辉煌纪录归在加尔文主义名下。毕察说:
对所谓自由派人士来说,有件奥秘他们始终不解,就是他们以为加尔文主义严苛专横、毫无弹性,但是这批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人居然一直最忠实、最勇敢地捍卫自由。这些人接受这个严峻的教义,但是这严峻的教义在他们心里产生的果效却是为自由效力,这真是让人想不透。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加尔文主义已经作到其它信仰一直作不到的事。加尔文主义向世人昭示人类的最高理想,并且以人所能想象的最惊人炮火一路扫荡,清除了一切障碍,使人能真正实现这个理想。
加尔文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人强烈感受到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不能依附于其它人事物。加尔文主义还以清晰夺目的大光照亮人心,使人看到他对神的责任、与永世的关系。人一进入世界就时时刻刻步向坟墓,但是加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有一个重责大任,就是「进天国,逃离地狱」,而这也成为他人生旅途中唯一的慰藉。
这样看来,加尔文主义者对人的看法是:「人被几个最强的力量驱使,这些力量在他里面产生压力与负担。他不是朝永生迈进、不久要到天上领受冠冕,就是躺在地狱里受炙热的痛苦,而且一直如此,直到永永远远」。谁敢禁锢这样的人?让开吧!不要拦阻他吧!否则要知道,这是会要你命的。让他自由吧!让他自己去找来到神面前的路吧!不要干涉他吧!不要干预他的权利吧!让他尽其所能,作成他自己得救的工夫吧!他的结局不是永恒的光荣,就是直到永永远远、无法形容的痛苦。谁也不能用高压手段对付这样的人。」(注十)
容我再引用另一位作者的的慷慨陈词:
加尔文主义好象一棵树,在有成见的人眼中,树皮粗硬,树干多瘤,树枝盘错,有如打结,外观虽然有力,却甚不体面。但是别忘了,这不是一棵昨天才长成的新柳。这些树枝已经和暴风雨奋斗千年了,树干被闪电遍吻,留下雷击之痕,树皮则满布战斧与子弹的痕迹。这棵老橡树没有柔细的典雅气质,外表也比不上温室植物的光滑,但是它的威严超过典雅,雄伟胜过美容。树根扭曲的样子也许很奇怪,但是有些树根里充满光荣的血泊,是参与无数大小战役所流下的,有些树根紧缠于殉道者的火刑柱,有些树根隐藏于幽居小室和孤寂的图书馆,有深度的思想家在其中默想祈祷,有如启示录的拔摩孤岛。树根的主干前后缠绕,最后环绕在充满生命与慈爱的各各他十架下,合成一股。树枝也许有节有瘤,不太好看,却有人类历史与基督教文明中最丰硕有力的果实累累下垂、作为装饰。(注十一)
我们综观加尔文主义,觉得好象坐在一部大管风琴的键盘前:我们的手指触动键盘,音栓便逐渐开启抑扬器,直到完整的合音出现,显出庄严的和声。加尔文主义触及人生每一部乐曲,因为它先寻求造物主,并且把他放在第一,又在各处都见到他。综观加尔文主义又好象离开渊面,头上有天空如顶,整个永恒宇宙围绕我们心灵,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之上,到处都见到神。综观加尔文主义还好象站在岩石缝隙上,地上景物在后,峡谷在前,时间的洪流澎湃,从亘古到永恒,太阳正顶头在天,到处满了它的热气,我们的心也与保罗同叹:「深哉!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因为加尔文主义把神显明给我们,又寻其踪迹,让我们看到神真是何等伟大,何等威严,至智慧、至圣洁、最公义、极慈爱。加尔文主义让我们看到神是至高者,我们的的心也再次赞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这不是对加尔文主义虚浮空洞的歌功颂德。有了上面这些事实与观察,每位不被蒙蔽的公正之士读了历史,都会同意我们所说的。再者,笔者也想借用司密斯博士在其著作《长老会信条》最后一章「结实累累的信条」中所说的:我们提出这些事实与观察,「不是要激发宗派的虚荣,而是要使我们因为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美景充满感恩,这也应该使我们更能站立在一个能够得尊荣的有利地位上。我们提出这些事实与观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心中点燃圣洁的火,使我们热切追求神所赐的信仰体系,内中有真理,并且在神的带领之下,成为创建美国与现代世界的最主要因素。」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作一个结论:读者已经在本书发现一些对神非常古老的描述──古到比圣经写作之时更古,老到比世界本身更老,因为这救赎计划是隐藏在神永远的旨意中。本书所主张、所护卫之教义实在奇妙,大大震撼人心,笔者并不打算隐藏这个事实。沉睡的罪人以为一生中任何时刻都可以随意与神和好,本书所阐述的事实足以使他们猛然惊醒。还有一些沉睡的「圣徒」满足于肉体的宗教,身陷致命的安逸却依然自欺,本书也应该能把他们吓醒才对。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感惊愕呢?自然界不是充满各样的奇事吗?为什么连启示也不能使他们惊异呢?我们只要略读一二就会明白,科学固然使人得知许多惊人的真理,但是未受教育的人会觉得这些真理很难相信,或者根本不能相信。属世领域如此,属灵领域又何尝不然?神启示的真理碰到属灵上未受教育的人也是如此。如果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不能令他惊奇、战栗、觉得不可思议,这福音就不是真福音。但是有谁曾经听了阿民念主义说「每个人的命运是自己勾勒出来的」之后会觉得惊奇呢?如果有人盲从大众的看法,一味忽视甚至讥诮加尔文主义,那是不够的。我们应该问:这教义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为什么要嘲笑它?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就证明它不真吧!最后我们要用一句话作为本书的结尾:这个被称作「加尔文主义」的伟大信仰思想体系正是世界的希望,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则太少。
(注一) E. W. Smith, The Creed of Presbyterians, p.52.
(注二) 同上,p.74.
(注三) McFetridge, Calvinism in History, p.113.
(注四) Hughes, Presbyterians and the Revolution, p. 140.
(注五) Warburton, Calvinism, p.78.
(注六) Froude, Calvinism, p.7.
(注七) Froude, Calvinism, p.8.
(注八) McFetridge, Calvinism in History, pp.151-153.
(注九) Loetscher, Address before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1929.
(注十) H. W. Beecher, Plymouth Pulpit, Article, Calvinism.
(注十一) Power and Claims of a Calvinistic Literature, p.35. 引自 Smith, The Creed of Presbyterians, p.105.